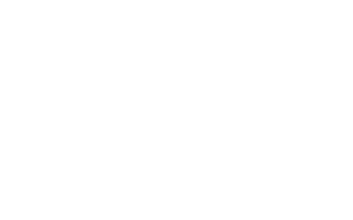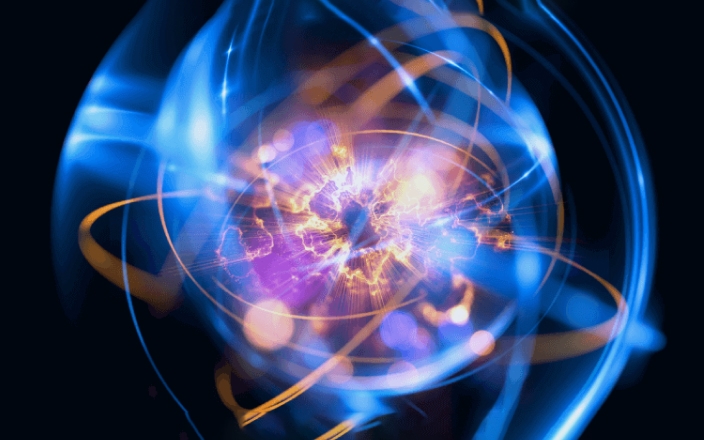临床前药代动力学研究是新药研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常会使用各种品种的啮齿类动物(大鼠、小鼠、豚鼠和地鼠等)来开展各类临床前药代动力学研究,借此来评估待测药物在体内的吸收(Absorption)、分布(Distribution)、代谢(Metabolism)和排泄(Excretion)过程。在啮齿类动物药代动力学研究中,为了满足部分特殊实验的需求,在实验开展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使用麻醉药物来促使动物处于麻醉或镇定状态(例如鞘内给药、颌下腺注射及微透析实验等)。本文将分别从麻醉药的背景,啮齿类动物麻醉方案及麻醉期间的药物相互作用等方面进行阐述,介绍麻醉药在啮齿类动物药代动力学研究中的相关应用策略与方法。
一、麻醉相关背景介绍
麻醉是通过使用药物或其它方法,对神经系统产生可逆性抑制,使患者整体或局部暂时失去感觉,以达到无痛的目的,为手术治疗或者其它医疗检查、治疗提供条件。麻醉发展史可以分为古代麻醉、近代麻醉和现代麻醉。古代麻醉主要使用麻沸散、曼陀罗等中草药产生麻痹作用,一些古籍如《神农本草经》等有相关记载。1846年10月16日,美国医生威廉·莫顿首次成功实施了一例乙醚麻醉手术,这标志着近代麻醉史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进入现代麻醉,麻醉开始进入学科专业化,麻醉药种类也变得多样化,麻醉的安全性也大幅提升,麻醉的应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1]。
另外,麻醉与实验动物福利也息息相关,将麻醉应用于动物实验过程是提升动物福利的有效措施。《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和使用指南》、3R(优化、替代、减少)指导原则和《美国公共卫生署人道管理和使用实验动物政策》等法规指南中明确指出,需要采用适当的麻醉措施来减少动物在实验过程中的疼痛和痛苦反应。
二、啮齿类动物麻醉方案介绍
麻醉药的分类
如图1所示,麻醉药根据其作用范围可以分为全身麻醉药和区域阻滞或局部麻醉药。全身麻醉药根据给药方式可以分为吸入麻醉药(一氧化二氮、异氟烷等)和注射麻醉药(戊巴比妥钠、氯胺酮、丙泊酚等)。局部麻醉药分为酯类比如丁卡因和酰胺类比如利多卡因等。还有一些药物,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麻醉药,而是经常和麻醉药联合使用,来获得更好的麻醉效果,或者满足一些其他的术前操作需求,比如一些常见的镇定、镇静、镇痛药以及肌松药等,可以将它们统称为麻醉辅助用药。

图1. 麻醉药的分类[1]
麻醉药的选择及麻醉方案的确立
目前可供使用的麻醉药种类繁多,根据各类麻醉药的特征,结合实验需求,兽医和实验人员会综合考虑以下因素,选择最优的麻醉药物使用策略:
使用方便,麻醉效果好;
副作用小,可使用对应解剂逆转麻醉作用;
药品级药物,价格合理;
在相同麻醉效果下,优先选择非管制药品。
不同的实验或不同的动物品系需要遴选最佳的麻醉方案,一般麻醉方案的确立过程为:查阅文献获取相关麻醉药的参考给药剂量;依据该剂量设置不同剂量梯度进行验证;观察动物麻醉效果(查看动物是否能进入手术麻醉期,是否麻醉过度等);最终确定最佳的给药剂量。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其它问题,会持续进行优化和更新。
三、麻醉期间的药物相互作用
动物在完成手术操作后,一般会给予一定的术后恢复时间才会应用到其他实验项目中,在项目开展当天麻醉药在动物体内已被完全清除,此时一般不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研究表明,药物相互作用多数发生在麻醉或者镇定与实验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比如颌下腺注射给药、舌下给药、关节腔注射、眼科给药、鞘内注射、各肠段直接注射给药和连续采集脑脊液等操作。
体内药代动力学主要涉及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即ADME四个过程。动物麻醉后,其胃肠动力、血浆蛋白置换作用、血脑屏障通透性、血流动力学、肝脏酶活性、肝脏血流量、肾功能和肾血流量等可能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待测化合物在动物体内的ADME过程产生影响[1],接下来分享几个相关案例。
麻醉对胃肠功能的影响
药物的吸收主要发生在胃肠道,文献调研结果显示使用异氟烷短暂麻醉动物(仅暴露6分钟)就会对其胃肠道蠕动产生影响,使其胃排空和肠蠕动变慢。以幽门为起点,跟未麻醉动物相比,标志物在肠道中前进距离下降大约50%[2]。而另一种注射麻醉剂舒泰50,无论是通过腹腔注射还是皮下注射,跟未麻醉动物相比,胃排空情况和胃容量变化都没有显著差异,如图2所示,说明舒泰50麻醉对动物胃功能基本没有影响[3]。所以对于需要在麻醉状态下开展的经胃肠道给药及相关研究,需谨慎使用异氟烷麻醉。

图2. 舒泰持续麻醉和未麻醉动物胃功能比较[3]
麻醉对原位肠灌注实验影响
在原位肠灌注实验中,动物需要全程处于麻醉状态,文献中选取了3种在肠道中通过被动扩散途径吸收的药物,分别是低渗透率的阿替洛尔、中等渗透率的美托洛尔和高渗透率的安替比林,探究了它们在四种不同的麻醉方案:戊巴比妥,氯胺酮/咪达唑仑,氯胺酮/赛拉嗪,氯胺酮/赛拉嗪/布托啡诺之下的肠道渗透率。实验结果表明,对于高渗透性药物安替比林,氯胺酮联合咪达唑仑麻醉下肠道的吸收效果最弱,而氯胺酮联合赛拉嗪加布托啡诺肠道吸收的效果最好,如图3所示。而且研究结果显示加上镇痛剂布托啡诺之后,因其减少了动物的疼痛应激,从而促进了药物肠道吸收,如图4所示。最终推荐氯胺酮/赛拉嗪/布托啡诺可作为原位肠灌注实验的标准麻醉方案[4]。

图3. 阿替洛尔、美托洛尔和安替比林在戊巴比妥、氯胺酮/咪达唑仑、氯胺酮/赛拉嗪、氯胺酮/赛拉嗪/布托啡诺麻醉下的渗透率比较[4]

图4. 不同麻醉方案下手术前后皮质酮水平差异的平均值[4]
麻醉对血脑屏障通透性的影响
异氟烷和氯胺酮是啮齿类动物药代动力学研究中常用的两种麻醉药。有文献报道异氟烷麻醉可使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增加,使部分药物在脑中的暴露量显著增加,而氯胺酮加赛拉嗪麻醉无此作用,如图5和图6所示。同时发现作用的机理是异氟烷影响了血脑屏障细胞膜的通透性,而不是影响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5]。因此,建议开展中枢神经系统(CNS)药物相关研究时,需谨慎使用异氟烷麻醉。

图5. 不同麻醉方案下蔗糖在脑中的药时曲线.Ket表示氯胺酮,ISO表示异氟烷[5]

图6. 不同麻醉方案0-4h内下蔗糖在脑中的AUC对比. Ket表示氯胺酮,ISO表示异氟烷[5]
麻醉对肝脏酶活性的影响
药物代谢主要借助于肝脏中细胞色素酶(也称为CYP酶,Cytochrome P450)发挥作用。有文献研究发现戊巴比妥钠和舒泰50均可提高肝脏中BROD酶(7-benzyloxyresorufin-O-debenzylase,7-苄氧基试卤灵-O-脱苄基酶,细胞色素酶家族中的一种活体形式)活性[6],如图7所示。而异氟烷麻醉无论是高浓度的短暂暴露,还是低浓度长时间持续的暴露(小于0.5%,每天吸入4h,持续30周),对细胞色素酶均没有影响[7]。所以在实验中需要综合考虑给药方式和待测化合物特性(如主要的代谢酶等)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案,将麻醉对实验影响降到最低。

图7. 用Telazol、替来他明、唑拉西泮或苯巴比妥麻醉对总CYP含量、BROD活性的影响[6]
麻醉对肾脏排泄的影响
药物排泄主要是在肾脏进行,大量的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常用的异氟烷或氯胺酮麻醉对于肾脏的结构、肾脏的功能、肾脏的血流量等都没有明显的影响,所以对于肾脏功能正常的动物,常规麻醉方式基本不会影响肾脏对药物的排泄功能[8-10]。
长效麻醉对淋巴插管实验的影响
迄今为止,超过40%的新活性化学物质是亲脂性的,并且表现出较差的水溶性。尽管它们具有良好的药理活性,但是受限于较低的口服生物利用度,而未能进入后续研发阶段,提高这些分子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药物肠淋巴系统转运能力。药物通过淋巴系统转运,除了能增加亲脂性分子的总体生物利用度之外,还具备其它的优势,比如避免肝脏首过代谢、改善药物的血浆分布等[11]。这类实验一般会使用淋巴插管动物模型(扩展阅读:解读丨大鼠肠系膜淋巴管插管模型验证渗透促进剂SNAC对淋巴吸收的影响),通过收集不同时间段的淋巴液进行分析,计算药物在淋巴系统的回收率。
此类实验目前一般有两种操作方式:第一种是短效麻醉后对动物实施淋巴插管手术,术后等待动物苏醒,恢复一段时间之后开展实验,称为清醒动物模型。第二种是短效麻醉后进行淋巴插管手术,之后通过颈静脉插管持续推注麻醉药物,使动物维持麻醉状态几小时,此种称为麻醉动物模型。文献研究了上述两种操作方式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在持续麻醉状态下,跟清醒动物相比,淋巴液流量显著下降,如图8所示[11]。淋巴液中药物的累计回收率,麻醉动物跟清醒动物相比下降25%左右,如图9所示[11]。此外该研究还做了两组对照,对照组动物不进行淋巴插管,其它实验操作一致。通过颈静脉采血分析,结果表明持续麻醉动物组与清醒组动物相较,血样中药物AUC下降25%左右,如图10所示[11]。这个实验发现很有意义,间接表明麻醉虽然会使淋巴液中药物含量下降,但是并没有影响药物吸收机制,即没有影响药物通过淋巴吸收途径和其它吸收途径的分配比。同时,麻醉状态下开展此类实验的成功率接近100%,也可降低动物的使用数量,更加适合于一些早期药物快速筛选实验。

图8. 清醒动物与麻醉动物淋巴液流量对比[11]

图9. 清醒动物与麻醉动物淋巴液中维生素D3累计回收率对比[11]

图10. 清醒动物与麻醉动物颈静脉血中维生素D3含量对比[11]
结语
麻醉药在啮齿类动物临床前药代动力学研究中应用广泛,为手术操作和一些特殊的实验开展提供保障,也很好地确保了动物福利。与此同时,因其部分药理效应,麻醉药也会给动物的生理功能带来一定影响,比如影响胃肠道动力、血脑屏障通透性、肝脏酶活性等,进而会影响待测化合物在体内的ADME过程。在临床前筛选研究中,可以结合待测化合物的给药方式、吸收方式、靶向部位和代谢途径等信息,选择合适的动物麻醉方式。期待麻醉学在实验动物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为临床前体内实验提供更多的选择,助力药物的研究和发展。
作者:严金玉,冯全利,董轩,焦桴荣,韩其岐,林丹清,董宇,汤城
编辑:方健,钱卉娟
设计:倪德伟,张莹莹
药明康德DMPK依托中国(上海、苏州、南京和南通)和美国(新泽西)的研发中心,提供从早期筛选、临床前开发、到临床研究阶段的综合型药代动力学服务,助力您快速推进药物研发流程。拥有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服务超1600家全球客户,具有超过十五年的新药申报经验,已成功支持超过1700个新药临床研究申请(IND)。
点击此处与我们的专家进行联系。
参考
[1] 邓小明等,现代麻醉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1年
[2] Torjman M C, Joseph J I, Munsick C, et al. Effects of isoflurane on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after brief exposure in ra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2005, 294(1-2): 65-71.
[3] Jordi J, Verrey F, Lutz T A. Simultaneous assessment of gastric emptying and secretion in rats by a novel computed tomography-based method[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Gastrointestinal and Liver Physiology, 2014, 306(3): G173-G182.
[4] Saphier S, Yacov G, Wenger A, et al. The Effect of Anesthetic Regimens on Intestinal Absorption of Passively Absorbed Drugs in Rats[J].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2020, 37: 1-10.
[5] Noorani B, Chowdhury E A, Alqahtani F, et al. Effects of Volatile Anesthetics versus Ketamine on Blood-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 via Lipid-Mediated Alterations of Endothelial Cell Membranes[J].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2023, 385(2): 135-145.
[6] Wong A, Bandiera S M. Induction of hepatic cytochrome P450 2B and P450 3A isozymes in rats by zolazepam, a constituent of Telazol®[J].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1998, 55(2): 201-207.
[7] European public MRL assessment report (EPMAR) Isoflurane (porcine species). Committee for Medicinal Products for Veterinary Use. 2018
[8] Ruxanda F, Miclaus V, Rus V, et al. Impact of isoflurane and sevoflurane anesthesia on kidne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rats[J]. Bulletin UASVM Veterinary Medicine, 2014, 71(2).
[9] Shiga Y, Minami K, Uezono Y, et al. Effects of the intravenously administered anaesthetics ketamine, propofol, and thiamylal on the cortical renal blood flow in rats[J]. Pharmacology, 2003, 68(1): 17-23.
[10] Bougherara H, Bouaziz O. Effects of the anaesthetic/tranquillizer treatments (Ketamine, Ketamine+ Acepromazine, Zoletil) on selected plasma biochemical parameters in laboratory rats[J]. Cent Eur J Exp Biol, 2014, 3(2): 1-5.
[11] Dahan A, Mendelman A, Amsili S, et al. The effect of general anesthesia on the intestinal lymphatic transport of lipophilic drugs: comparison between anesthetized and freely moving conscious rat models[J].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2007, 32(4-5): 367-374.
加入订阅
获取药物代谢与药代动力学最新专业内容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