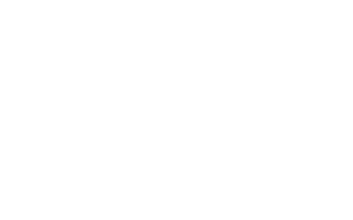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等生活方式的改变,全球眼部疾病患者的数量持续上升。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是老年人群低视力乃至失明的主要原因[1],已成为眼科领域增长潜力最大的方向之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作为常见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成人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糖尿病患病率的持续攀升,DR的影响人数也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2]。此外,免疫相关性眼病如葡萄膜炎、甲状腺眼病等,已成为影响青壮年视力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不断增长的眼科疾病治疗需求推动了更优治疗方案的研发与落地。当前,眼科创新药物市场正处于稳定快速增长阶段,据沙利文《眼科药物市场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预测,2025年眼科创新药物市场将达到464亿美元,2030年将达到739亿美元。本文基于已上市产品的研发案例,结合我们的经验积累,梳理了眼科蛋白类药物的现状及临床前药代动力学实验设计,旨在为该类药物的研发提供参考。
已上市眼科治疗性蛋白药物总结
自2006年雷珠单抗获批以来,眼科治疗性蛋白类药物研究成为热点,尤其在眼底血管疾病和免疫相关性眼病的治疗领域发展迅速。目前全球已累计获批约11款蛋白类眼科用药,包括抗原结合片段(Fab)、单抗、融合蛋白、单链可变片段(scFv)、双抗等不同的分子形式(图1),相关适应症包括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糖尿病黄斑水肿、视神经脊髓炎和甲状腺相关性眼病等。表1总结了目前已上市的眼科治疗性蛋白药物的作用靶点、骨架结构、给药途径和频率及适应症等信息。

图1. 眼科治疗性蛋白药物的分子形式[3]
在眼科药物市场中,眼底血管病变治疗药的份额最大,其中以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相关药物为主。VEGF是一种由二巯键相连的同源二聚体的糖蛋白,广泛分布于人体的脑、眼、肾、肝等组织器官,其中眼部的视网膜周细胞、内皮细胞、色素上皮细胞、神经节细胞等均可表达VEGF,在眼部血管完整性的维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VEGF分子家族包括5个成员,分别为VEGF-A、VEGF-B、VEGF-C、VEGF-D及胎盘生长因子(PLGF),其中VEGF-A最具活性,并与新生血管生成及血管通透性的增强关系密切[4]。VEGF过表达会导致新生血管异常增生,在眼科疾病中引发视网膜渗漏和水肿,严重损害患者视力。目前已获批上市的阿帕西普、康柏西普、雷珠单抗、布西珠单抗和法瑞西单抗均靶向VEGF(图2 a)[5]。除VEGF靶点外,阿达木单抗抑制TNF-α等促炎因子,诱导Treg细胞上升,修复视网膜屏障。依库珠单抗抑制C5补体介导的炎症反应起效。伊奈利珠单抗、利妥昔单抗和萨特利珠单抗作用于B细胞成熟分化过程中的各阶段,分别靶向CD19、CD20和IL-6,能抑制自身抗体的产生,从而使视神经细胞表面水通道蛋白4(AQP4)免受攻击(图2b, 2c)[6][7],替妥木单抗作用于眼眶组织中广泛表达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GF-1R),从而干预自身抗原促甲状腺激素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阻碍疾病进展[8]。
表1. 已上市的眼科治疗性蛋白药物*
通用名 | 商品名 | 靶点 | 药物形式 (分子量) | 骨架结构 | 给药途径(频率) | 适应症 | 公司 | 首次上市时间及国家 |
Ranibizumab 雷珠单抗 | Lucentis 诺适得 | VEGF-A | Fab (48 kDa) | Fab,无Fc端 | IVT (q4w) | wAMD,DME,RVO, CNV,DR,ROP | 诺华/罗氏 | 2006年,美国 |
Aflibercept 阿帕西普 | Eylea 艾力雅 | VEGF | 融合蛋白 (115 kDa) | 融合人源IgG1的Fc端 | IVT (q16w) | wAMD,DME, RVO, DR, ROP | 再生元/拜耳 | 2011年,美国 |
Conbercept 康柏西普 | 朗沐 | VEGF | 融合蛋白 (~142 kDa) | 融合人源IgG1的Fc端 | IVT (前3个月1月1次,后续每3个月1次) | wAMD,DME,RVO | 康弘药业 | 2013年,中国 |
Adalimumab 阿达木单抗 | Humira 修美乐 | TNF-α | 单抗 (~148 kDa) | 人源化IgG1 | SC (qw) | 非感染性葡萄膜炎 | 艾伯维/卫材 | 2016年,美国 |
Eculizumab 依库珠单抗 | Soliris 舒立瑞 | C5补体 | 单抗 (~148 kDa) | 人源化IgG2/4 | IV (qw) | NMOSD | 阿斯利康 | 2019年,美国 |
Brolucizumab 布西珠单抗 | Beovu 培优适 | VEGF-A | scFv (26 kDa) | 人源化单链抗体片段 | IVT (前三到五次每4-6周一次,后续8-12周一次) | wAMD,DME | 诺华 | 2019年,美国 |
Inebilizumab 伊奈利珠单抗 | Uplizna 昕越 | CD19 | 单抗 (~149 kDa) | 人源化IgG1 | IV (前两次每2周一次,后续6个月一次) | NMOSD | Viela Bio | 2020年,美国 |
Satralizumab 萨特利珠单抗 | Enspryng 安适平 | IL-6R | 单抗 (~143 kDa) | 人源化IgG2 | SC (前三次每2周一次,后续1个月一次) | NMOSD | 罗氏/中外制药 | 2020年,日本 |
Teprotumumab 替妥木单抗 | Tepezza | IGF-1R | 单抗 (~148 kDa) | 人源化IgG1 | IV (q3w) | 甲状腺相关性眼病 | 安进 | 2020年,美国 |
Faricimab 法瑞西单抗 | Vabysmo 罗视佳 | VEGF-A/Ang2 | 双抗 (146 kDa) | 人源IgG1,更改了Fc端不能结合FcR,靶向VEGF的Fab和雷珠单抗相同 | IVT (每4周一次,至少4次,后续给药间隔可延长达16w) | wAMD,DME,RVO | 罗氏 | 2022年,美国 |
Rituximab 利妥昔单抗 | Ristova 美罗华 | CD20 | 单抗 (145 kDa) | 人源的IgG1的恒定区和小鼠的可变区 | IV (qw或q2w) | NMOSD | 罗氏/Biogen | 2022年,日本 |
*未统计生物类似药。
备注:VEG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PLGF: placental growth factor,胎盘生长因子;VEGFR,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ANG: an-giopoietin, 血管生成素; IGF-1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SC: subcutaneous injection,皮下注射;IV: intravenous injection,静脉注射;IVT: intravitreal injection,玻璃体腔注射;qw: quaque-week,每周给药一次;q2w: 2周一次;q3w: 3周一次;q4w:4周一次;q16w: 16周一次。wAMD: wet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DME: diabetic macular edema. 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R: diabetic retinopathy,糖尿病视网膜病变;CNV: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继发的黄斑水肿及脉络膜新生血管;
RVO: Retinal vein occlusion,视网膜静脉阻塞;ROP: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早产儿视网膜病变;NMOSD: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 视神经脊髓炎;
![(a) 抗VEGF治疗眼科疾病的作用机制(Bevacizumab用于非标签(off-label)的治疗)[5];(b) 伊奈利珠单抗、萨特利珠单抗和依库珠单抗保护神经细胞机制[6];(c)利妥昔单抗、伊奈利珠单抗和萨特利珠单抗分别作用于B细胞发育的不同阶段 (a) 抗VEGF治疗眼科疾病的作用机制(Bevacizumab用于非标签(off-label)的治疗)[5];(b) 伊奈利珠单抗、萨特利珠单抗和依库珠单抗保护神经细胞机制[6];(c)利妥昔单抗、伊奈利珠单抗和萨特利珠单抗分别作用于B细胞发育的不同阶段](https://wuxiapptec-dmpkcatalog-prod.oss-cn-shanghai.aliyuncs.com/Public/Uploads/ueditor/upload/image/20251021/1761032215436480.jpg)
图2. (a) 抗VEGF治疗眼科疾病的作用机制(Bevacizumab用于非标签(off-label)的治疗)[5];(b) 伊奈利珠单抗、萨特利珠单抗和依库珠单抗保护神经细胞机制[6];(c)利妥昔单抗、伊奈利珠单抗和萨特利珠单抗分别作用于B细胞发育的不同阶段[7]。
眼科治疗性蛋白药物临床前药代动力学考量
眼科治疗性蛋白药物的临床前药代实验设计和其给药途径密切相关。如果是系统途径给药,可参考常规的蛋白类药物临床前药代动力学研究方法,只需在相关动物种属中开展PK研究,一般选择2个或2个以上剂量。如果药物在临床上采用SC给药途径,则需要开展IV和SC两种给药途径的动物PK研究。如表2所示,阿达木单抗、依库珠单抗、伊奈利珠单抗、萨特利珠单抗和替妥木单抗均只开展了系统给药途径下的动物PK研究。如果药物的临床给药途径是IVT(intravitreal injection, 玻璃体腔注射)给药,则建议开展动物IVT给药的血清PK和眼组织分布研究。IVT给药虽然是一种有创的给药方式,但注射后可使玻璃体的药物浓度达到较高水平,是多种眼底病的有效给药途径。目前获批上市的玻璃体腔注射的蛋白类药物包括雷珠单抗、阿帕西普、康柏西普、布西珠单抗和法瑞西单抗(表3)。
表2. 5个系统途径给药的眼科蛋白药物临床前PK实验设计*
通用名 | 临床给药途径 | 临床前PK研究 | 具体测试内容 | 毒理种属 |
Adalimumab 阿达木单抗[9] | SC | 食蟹猴IV 和SC单剂量单次给药PK | 血清PK和ADA检测 | 食蟹猴、大鼠和小鼠 |
食蟹猴IV单剂量和3个SC剂量单次给药PK | 血清PK和ADA检测 | |||
小鼠IV单次给药PK | 血清PK | |||
Eculizumab 依库珠单抗[10] | IV | C5缺失的小鼠IV单剂量和SC单剂量单次PK | 血清PK和血清PD指标 | 小鼠 |
Inebilizumab 伊奈利珠单抗[11] | IV | huCD19转基因小鼠IV给药,两个剂量单次给药PK | 2个剂量,结合在毒理实验中开展 | huCD19转基因小鼠 |
Satralizumab 萨特利珠单抗[12] | SC | 食蟹猴4个剂量的单次给药PK (IV和SC各2个剂量) | IL-6和血清PK、ADA检测 | 食蟹猴 |
Teprotumumab 替妥木单抗[13] | IV | 3个剂量的雄性大鼠IV单次给药PK, 4个剂量的双性别食蟹猴IV单次给药PK | 血清PK和ADA检测 | 食蟹猴 |
雄性食蟹猴中的PK/PD实验 | 血清PK、ADA,及PD (IGF1R) 指标检测 |
*利妥昔单抗已有多个适应症获批,在日本上市用于NMOSD适应症未查询到临床前相关药代实验。
备注:PK: pharmacokinetics,药代动力学;ADA: anti-drug antibody, 抗药抗体;PD: Pharmacodynamics,药效动力学;C5: Complement Component 5,补体C5; IL-6, Interleukin-6, 白细胞介素-6。
表3. 4个IVT给药的眼科蛋白药物临床前PK实验设计*
通用名 | 临床给药途径 | 临床前PK研究 | 具体测试内容 | 毒理种属 |
Ranibizumab 雷珠单抗[14] | IVT | 雄性新西兰大白兔双眼IV给药,两个剂量 | 血清中的药物浓度检测 | 食蟹猴和新西兰大白兔 |
雄性新西兰大白兔双眼IVT双眼给药,两个剂量 | 玻璃体、房水、血清中药物浓度检测,玻璃体、血清中的ADA检测 | |||
125I标记的抗体用于雄性新西兰大白兔眼组织分布,IVT双眼给药 | 采集眼球(3个时间点) | |||
新西兰大白兔IVT, 结膜下注射、前房双眼注射单次PK比较(预试) | 采集玻璃体、房水和视网膜并检测药物浓度(各2个时间点) | |||
新西兰大白兔IVT, 结膜下注射、前房双眼注射单次PK比较 | 采集玻璃体、房水、视网膜和血清并检测药物浓度(各6个时间点) | |||
雌雄食蟹猴IVT和IV单次PK,各两个剂量 | 玻璃体液、视网膜、房水和血清中的药物浓度检测 | |||
Aflibercept 阿帕西普[15] | IVT | 色素兔IVT单次PK | 玻璃体、视网膜、脉络膜、血清中的药物浓度检测 | SD大鼠和食蟹猴 |
食蟹猴的IV(单组)和SC(四组)单次给药PK,双性别 | 血清中的药物浓度检测 | |||
125I标记的阿帕西普用于雌性SD大鼠组织分布,IV给药 | 采集主要组织器官检测放射性 | |||
肾切除和假手术SD大鼠IV单次PK比较 | 评估肾脏对药物的清除作用 | |||
Brolucizumab 布西珠单抗[16] | IVT | 食蟹猴IV单次给药,双性别 | 血清PK和ADA检测 | 食蟹猴 |
新西兰大白兔单眼IVT单次给药的血清PK和眼组织PK | 1.采集玻璃体液、视网膜、脉络膜、房水、血清并测定药物浓度的检测;未评估ADA; 2.在给药前及给药后24、72、144和288小时安乐前对兔子眼睛进行裂隙灯和间接检眼镜检查 | |||
食蟹猴单眼IVT单次给药后的眼科PK(预试) | 采集中央视网膜、周边视网膜、玻璃体液、房水、中央脉络膜、周边脉络膜、血清中药物浓度(7个时间点)及部分动物的血清ADA检测。 | |||
食蟹猴单次IVT给药后的眼科PK(剂量、给药体积和溶媒考察) | 采集中央视网膜、周边视网膜、玻璃体液、房水、中央脉络膜、周边脉络膜、血清,并检测所有样品药物浓度和血清ADA | |||
Faricimab 法瑞西单抗[17] | IVT | 新西兰大白兔IV单次给药的血清PK,两个剂量 | 血清中药物浓度和ADA | 食蟹猴 |
食蟹猴单次IV和IVT给药后的血清PK和主要眼组织PK | 玻璃体液、房水、血清PK,血清ADA检测 | |||
色素兔IVT单次给药的血清PK和主要眼组织PK | 玻璃体液、房水、血清PK,血清ADA检测 | |||
食蟹猴单次IV和IVT给药后的血清PK和主要眼组织PK | 房水、血清PK,房水和血清ADA检测 |
*未查询到康柏西普临床前药代实验设计。
IVT给药一般选择兔子作为PK研究的动物种属之一,主要原因是兔眼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结构与人眼相似,且兔种属眼球大,便于进行IVT给药操作和观察,有成本低和易获得等优势[18]。在目前获批的4款IVT给药药物的申报中,均使用了兔子进行IVT给药后采集主要眼部组织并分析这些组织中的药物浓度。需要注意的是,兔子可作为眼部组织分布研究的一个合适的动物种属,但不一定能够作为毒理研究的相关动物种属,例如布西珠单抗,体外结合活性实验显示兔子并不是相关动物种属。因此,在布西珠单抗的临床前研究中也只选择了食蟹猴作为相关动物种属进行毒理研究。综合考虑兔子和食蟹猴的眼部生理学和解剖学优势,眼科治疗性蛋白类药物通常会选择兔子和猴子两种动物种属考察药物在眼部的各个细分组织分布情况。常规的新西兰大白兔属于白化动物,眼内缺乏黑色素,与人眼富含黑色素不同。黑色素缺失可能影响药物在眼内的分布(扩展阅读:药物与黑色素结合的体外研究方法及意义),阿帕西普和法瑞西单抗均使用了色素兔开展IVT给药后的眼组织的PK研究。另外,由于兔子极易产生抗药抗体,抗药抗体会严重影响药物在体内的暴露量,导致兔子可能不适合作为毒理实验的动物种属。如法瑞西单抗在PK实验中使用了兔子,在毒理实验中因易产生抗药抗体而未使用兔子作为毒理种属。
动物经IVT给药后眼部细分组织的吸收、分布和消除数据可用于预测药物在人体眼睛各个细分组织的浓度。在雷珠单抗的开发过程中,研发人员根据兔子和猴子经IV和IVT两种给药途径下的药代数据,建立了6房室模型(图3)[14]。对于IV给药途径,血清药物浓度可根据2房室模型预测。对于IVT给药途径,眼睛分成4个房室:玻璃体中心(房室3)、玻璃体(房室4)、前房(房室5)和视网膜(房室6)。兔子和猴子经IVT给予雷珠单抗后,玻璃体和视网膜的药物浓度比值是比较相似的,血清药物浓度均比玻璃体药物浓度低1000倍以上,并且在不同剂量下组织和血清的药物浓度呈现剂量依赖性。这个模型被证明能很好的预测其他剂量下兔子和猴子的视网膜和血清中的药物浓度,为后续预测人体眼部PK提供了强力支持。目前针对IVT给药,已有文献报道了多个不同的房室模型[19],可针对具体药物的特点,建立合适的模型来预测人体眼部PK。

图3. 雷珠单抗眼部PK的房室模型[14]
2020年9月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颁发了《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治疗药物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20]。对于眼科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提出如下要求和建议:对于眼局部给药(例如:玻璃体内注射给药)的药物,需评估药物局部暴露和系统暴露。对于存在系统暴露或者通过系统途径给药的药物,可参考常规的系统药代动力学的研究方法,提供该药物的系统暴露情况以及药物代谢、消除等时间动力学过程的数据。对于主要分布在眼局部且局部起效的药物,建议提供相关的动物眼局部药物代谢动力学的数据,包括药物在房水、玻璃体液等部位的分布、代谢和消除过程。鼓励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放射性同位素分子影像技术以及药代动力学模型/模拟技术等。
结语
目前主流的眼部药代实验需要使用较多动物,以获取各眼部细分组织的药物浓度数据。考虑到动物使用的3R原则,可以使用定量全身放射自显影技术 (quantitative whole-body autoradiography, QWBA)和影像学技术来大幅降低动物的使用数量。一些新技术也不断涌现,如眼部微透析技术,可用于玻璃体内给药后的药物浓度的持续采样和分析[21]。药明康德DMPK已建立临床前动物眼科药代评价平台,能够熟练操作临床前大小动物的各种眼局部给药、各种眼部细分组织的样品采集和药物浓度分析。药明康德DMPK的QWBA平台可用于评价眼科药物在临床前动物眼部各精细组织的分布情况,为客户的新药研发提供助力。
作者:程起干,侯丽娟,孙建平,刘欢,金晶
编辑:钱卉娟,富罗娜·克里木
设计:倪德伟,张莹莹
药明康德DMPK依托中国(上海、苏州、南京和南通)和美国(新泽西)的研发中心,提供从早期筛选、临床前开发、到临床研究阶段的综合型药代动力学服务,助力您快速推进药物研发流程。拥有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服务超1600家全球客户,具有超过十五年的新药申报经验,已成功支持超过1700个新药临床研究申请(IND)。
点击此处与我们的专家进行联系。
参考
[1] Rein DB, Wittenborn JS, Burke-Conte Z, Gulia R, Robalik T, Ehrlich JR, Lundeen EA, Flaxman AD. Prevalence of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in the US in 2019. JAMA Ophthalmol. 2022 Dec 1;140(12):1202-1208.
[2] 刘涵,方晏红,陈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全科医学管理,眼科学报,2023年4月,第38卷,第4期:350-359。
[3] Tatsumi T. Current Treatments for Diabetic Macular Edema. Int J Mol Sci. 2023 May 31;24(11):9591.
[4] Pożarowska D, Pożarowski P. The era of anti-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drugs in ophthalmology, VEGF and anti-VEGF therapy. Cent Eur J Immunol. 2016;41(3):311-316.
[5] Heloterä H, Kaarniranta K. A Linkage between Angiogenesis and Inflammation in 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Cells. 2022 Nov 1;11(21):3453.
[6] Selmaj K, Selmaj I. Novel emerging treatments for NMOSD. Neurol Neurochir Pol. 2019;53(5):317-326.
[7] Pittock SJ, Zekeridou A, Weinshenker BG. Hope for patients with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 - from mechanisms to trials. Nat Rev Neurol. 2021 Dec;17(12):759-773.
[8] Jain AP, Jaru-Ampornpan P, Douglas RS. Thyroid eye disease: Redefining its management-A review. Clin Exp Ophthalmol. 2021 Mar;49(2):203-211.
[9]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02/BLA_125057_S000_HUMIRA_PHARMR.PDF
[10]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07/125166s0000_PharmR.pdf
[11]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20/761142Orig1s000PharmR.pdf
[12]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20/761149Orig1s000PharmR.pdf
[13]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21/761143Orig1s000PharmR.pdf
[14]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06/125156s0000_Lucentis_PharmR.pdf
[15]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11/125387Orig1s000PharmR.pdf
[16]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19/761125Orig1s000PharmR.pdf
[17]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22/761235Orig1s000PharmR.pdf
[18] 付淑军, 于 冰, 廖 琴, 孙 涛, 经眼玻璃体给药药物的研究进展及非临床研究的考虑要点, 药学学报, 2023, 58(4): 815−825。
[19] Agrahari V, Mandal A, Agrahari V, Trinh HM, Joseph M, Ray A, Hadji H, Mitra R, Pal D, Mitra AK. A comprehensive insight on ocular pharmacokinetics. Drug Deliv Transl Res. 2016 Dec;6(6):735-754.
[2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0年9月,《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治疗药物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1] Boddu SH, Gunda S, Earla R, et al. Ocular microdialysis: a continuous sampling technique to study pharmacokine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 in the eye [J]. Bioanalysis, 2010, 2: 487-507.
加入订阅
获取药物代谢与药代动力学最新专业内容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