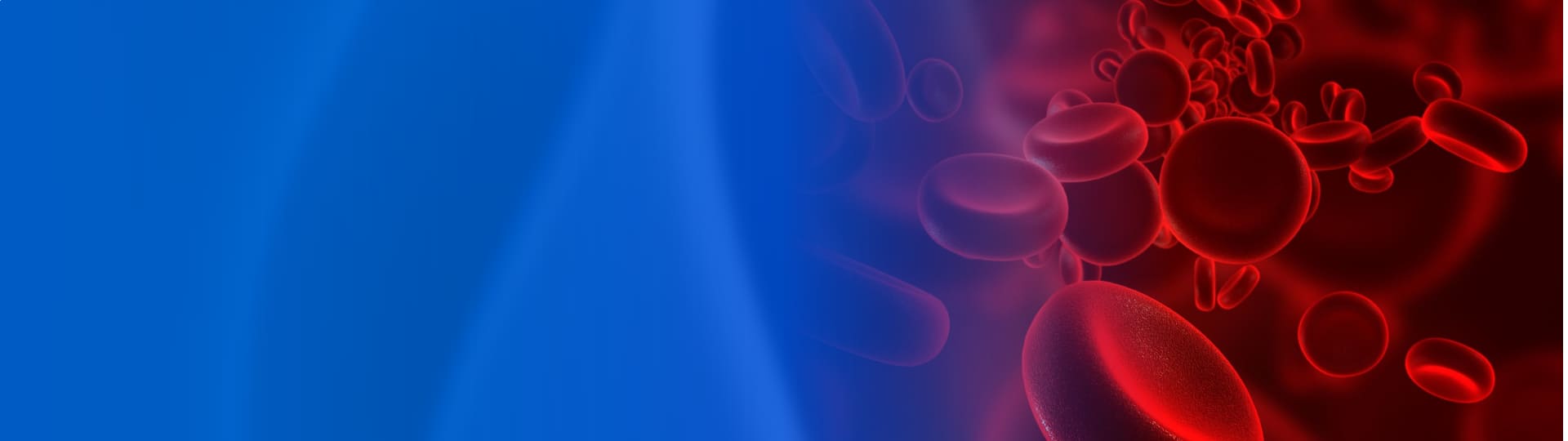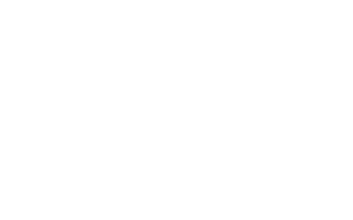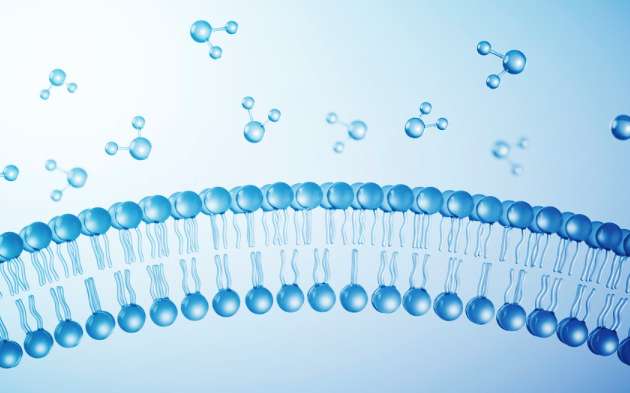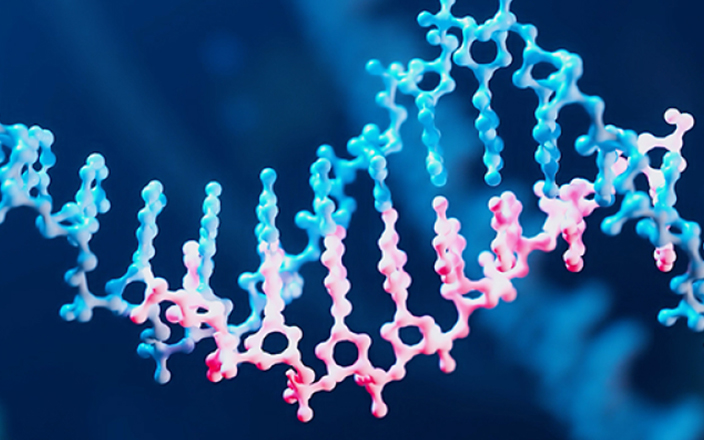在现代药物研发中,准确预测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性是保障药物安全有效的关键步骤,血浆蛋白结合(plasma protein binding, PPB)是其中的重要研究之一。药物与血浆蛋白的结合能力决定了游离药物,即未结合药物的比例(fu)。游离药物能够穿过细胞膜与靶点结合,并被代谢或排泄,其比例直接影响药物的分布和清除[1],特别是肝脏清除率。因此,药物的游离分数是预测肝脏清除率的重要参数,同时血浆蛋白结合率也是预测药物代谢酶和转运蛋白抑制和诱导的关键输入参数,是评估药物相互作用(dug-drug interaction)风险的关键因素之一。ICH M12指导原则指出,对高结合药物(fu<0.01),历史上使用默认下限值0.01是为了避免DDI预测的假阴性结果。为更科学地评估药物的实际药物相互作用风险,应选择适当方法准确测定其蛋白结合率。此外,药物间的血浆蛋白结合位点竞争可能改变游离药物比例,影响疗效或引发不良反应。因此,准确了解药物的PPB特性对预测和管理DDI至关重要[2]。本文系统阐述了测定挑战性化合物血浆蛋白结合(PPB)的方法及策略,并重点介绍血浆蛋白结合率的准确测定对预测药物相互作用(DDI)的重要性。
血浆蛋白结合(PPB)测定的方法学挑战与策略
血浆蛋白结合是药物发现和开发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其原理为药物分子在体内可以可逆地与血浆和组织中的蛋白质和脂质结合,未结合的药物分子可自由穿过细胞膜扩散,进而与治疗靶点或其他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图1)。在多数情况下,化合物结合度非常高并不能判断其好坏,但PPB实验测到的游离分数(fraction unbound,fu)却是一种需要准确测定的关键参数,它对于预测药物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作用[2]。针对高结合化合物,测定准确的fu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药明康德DMPK已经建立了测定高结合化合物的多种方法,如预饱和法,超速离心法,稀释血浆法,动态透析法等(见文章:高蛋白结合药物PPB测定:动态透析法的原理及优势),可通过两种方法联用获得准确fu。

图1. 游离药物假说[3]
高PPB化合物测定的准确性评估
研究人员选用两种典型的高血浆蛋白结合药物—华法林(抗凝剂)和伊曲康唑(抗真菌药)作为模型化合物,通过多实验室协作研究系统,评估了不同方法测定高结合药物PPB的准确性。来自9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采用平衡透析(包括HTD和RED)、超速离心及超滤等多种方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测定了华法林的游离分数。研究数据表明,人血浆中华法林的平均fu值为0.011(范围:0.005-0.017),与文献报道值0.014高度吻合。同时,来自11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通过方法优化测得伊曲康唑的平均fu值为0.0015(范围:0.0007-0.0022),也与文献值0.0020相符[4]。该研究结果证实,优化实验条件可获得与文献值高度吻合的fu测定值,为高结合药物的DDI研究提供可靠的方法学基础。
挑战性化合物的实验策略优化
测定化合物在生物基质中的游离分数有多种方法,如平衡透析法、超速离心法、超滤法等,其中平衡透析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但其可靠性受限于以下因素:体系是否达到充分平衡、待测化合物的溶解特性,以及缓冲液中游离样品的浓度是否满足分析灵敏度的要求。对于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化合物,需根据化合物性质等选择合适的方法,如高度结合的亲脂酸、水溶性较差的亲脂化合物、高分子量和扩散慢的化合物,可采用预饱和法、稀释法和动态透析法等策略。但对于某些化合物如共价抑制剂,超滤或超离心可能更合适。虽然精确测量化合物PPB具有挑战性,但通过方法优化,可准确测定fu < 0.01的挑战性化合物。(见图2)

图2. 测定高结合化合物方法的决策树[2]
血浆蛋白结合(PPB)在药物相互作用预测中的应用
准确测量PPB对于预测人类药代动力学(PK)、DDI、毒性指数(TI)估计以及PK/PD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系统性分析表明,PPB对理解候选药物的重要特性,尤其在DDI中具有显著影响,因为它提供了临床DDI风险和研究设计的见解。对于高蛋白结合药物(fu < 1%),ICH M12指南允许采用实验测定的真实fu值进行预测,显著提高了预测准确性。
临床DDI风险评估的一般原则
监管机构的指导文件为评估DDI潜力提供了系统性框架,建议采用从简单静态模型到复杂机制模型的递进式预测策略,以更准确地评估潜在的临床影响。在将体外抑制/诱导数据外推至体内DDI预测时,PPB对临床DDI效应的估算具有关键作用。历史上,各监管机构普遍推荐在DDI预测中采用0.01作为fu的下限值,但这一保守设定易高估高结合药物的临床DDI风险[5]。以下四个案例研究对比了使用0.01的fu下限值与实际测量fu值对DDI预测幅度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
案例1
Fahmi等(2009)[7]的研究表明,伊曲康唑(血浆蛋白结合率> 99.7%,实测fu = 0.001-0.003)作为CYP3A4强抑制剂,其DDI预测高度依赖游离药物浓度的准确估算。当采用实际测量fu值(0.001-0.003)进行预测时,伊曲康唑与咪达唑仑(CYP3A4底物)的相互作用预测AUC增加幅度为5-10倍,与临床观察数据吻合良好;而若采用此前监管机构默认的0.01 fu下限值,由于高估了游离药物浓度约3-10倍,导致预测的AUC增幅被放大至10-30倍,显著偏离真实临床情况。这一对比证实,对于极高蛋白结合率的药物(fu<0.01),机械性地采用0.01的fu下限会引入保守性偏差,可能造成临床DDI风险的过度预估。研究建议对此类特殊药物应采用实测fu值或PBPK模型进行精准预测。
表1. 伊曲康唑fu实测值预测DDI结果
Precipitant | Precipitant Dose | Precipitant Dose Interval | Dose Type | [I]= Csys | Measured fu | Midazolam Dose | Dose Type | Observed DDIa | References |
Itraconazole | 200mg (4 days) | q.d. | p.o. | 0.270 | 0.002 | 7.5mg | p.o. | 10.8 | Olkkola et al., 1994 |
Itraconazole | 100mg (4 days) | q.d. | p.o. | 0.128 | 0.002 | 7.5mg | p.o. | 5.74 | Ahonen et al., 1995 |
Itraconazole | 200mg (6 days) | q.d. | p.o. | 0.270 | 0.002 | 7.5mg | p.o. | 6.64 | Olkkola et al., 1996 |
Itraconazole | 200mg (4 days) | q.d. | p.o. | 0.270 | 0.002 | 7.5mg | p.o. | 6.16 | Backman et al., 1998 |
案例2
在一例肿瘤治疗药物通过抑制肾脏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OAT1/OAT3引发药物相互作用的案例中[4],当采用实测游离分数值0.008并通过静态模型评估药物相互作用风险时,游离药物浓度未达到EMA指南推荐的Ki/50的阈值,因此未预测出具有临床意义的相互作用。然而,当采用0.01的游离分数下限值,结合50倍安全阈值进行评估时,则提示需要在临床药物相互作用研究中进一步评估潜在风险。由于肿瘤药物开展临床相互作用研究往往存在实际困难,最终药品说明书中仍纳入了与OAT1/OAT3底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的警示,这可能导致部分原本可能获益的癌症患者无法使用该药物。采用0.01的游离分数下限值(而非更低的实测值)评估高蛋白结合化合物的相互作用风险,会导致更为保守的药品标签要求。
案例3
如表2所示[4],一个处于早期发现阶段的化合物因抑制肝脏OATP1B1转运蛋白,而被评估为有DDI风险。根据2012年美国FDA药物相互作用指南提供的公式计算R值:研究同时采用实测游离分数值与0.01下限值来评估临床相互作用风险。当采用0.01的游离分数下限时,预测将产生显著的临床相互作用(AUCR=6.1,假设FT,OATP=1,即药物完全依赖OATP1B1进入肝细胞),但该结果严重高估了实际临床观察值(AUCR=1.8);而采用实测游离分数值预测时,结果更为准确(AUCR=2.0)(见表2)。该案例进一步强调,使用0.01的fu下限过于保守,可能会过高估计临床DDI风险。
Iin,max=Cmax+(Ka X Dose X FaFg) / Qh
R-value=1+(fuX Iin,max/IC50)
备注:R为底物药物的AUC比值,fu为抑制剂在血液中的游离分数,Iin,max为抑制剂在门静脉中的预估最大浓度(假设ka=0.1 min-1且FaFg=1),IC50为抑制剂的半数抑制浓度,Cmax为抑制剂在血浆中的最大浓度,Ka为吸收速率常数(假设为0.1 min-1,此为通用假设),Dose为抑制剂的给药剂量,FaFg为抑制剂被吸收的剂量分数,假设为1(即完全吸收且无肠道代谢),Qh为肝血流量。
表2. 药物的fu实测值和0.01 fu下限值预测DDI结果比较
OATP1B1 IC50 (μmol/L) | 测定的fu | 使用0.01作为下限fu预测的R值 | 使用实际测定fu预测的R值 | 观察到的临床DDI (AUC倍数) |
0.172 | 0.002 | 6.1 | 2.0 | 1.8 |
案例4
孟鲁司特(Montelukast)是一个高度结合的药物,其血浆未结合分数(fu)值极低,为0.000051。在过去,监管机构为了保守起见,将所有高度结合药物的fu值设定为1%进行DDI预测。对于孟鲁司特,如果按照这个设定值,会导致其CYP2C8抑制的曲线下面积比(AUCR)达到1.89,暗示可能存在临床相关的药物相互作用。然而,在临床口服给药的实践方案中,孟鲁司特并没有观察到与罗格列酮(CYP2C8底物)和瑞格列奈(CYP2C8底物)的明显药物相互作用。这表明,使用1%的血浆fu下限可能会高估孟鲁司特CYP2C8 DDI的风险。反之,如果使用实验得到的真实fu值(0.000051)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没有药物相互作用发生,这与临床观察结果一致[6]。这个例子突显了实验测量的fu在准确预测DDI中的重要性。
置换相互作用的特殊考量
血浆蛋白结合置换作用可直接影响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当多种药物同时使用时,它们可能竞争相同的血浆蛋白结合位点,导致游离药物浓度发生改变,进而影响疗效或增加不良反应风险。准确测定PPB对预测药物相互作用至关重要,有助于指导临床用药决策和药物研发。在联合用药时,若两种药物结合相同的血浆蛋白,了解其PPB特性可帮助预测潜在相互作用,从而调整剂量或选择替代药物。虽然PPB置换作用在临床上通常影响有限,但对于某些特定药物(如fup <0.1、治疗窗窄、肝提取率高或静脉给药的药物)仍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例如,华法林与苯丁酮联用导致的凝血异常,以及磺胺类药物与甲苯磺丁脲联用引发的严重低血糖,都被认为与血浆蛋白置换作用相关[2,5]。

图3. 评估血浆蛋白结合置换相互作用对临床重要性的决策树[2]
小结
血浆蛋白结合率的精准测定是药物研发的核心环节,其直接影响药物相互作用的评估。研究表明,在严格优化实验条件的前提下,现有PPB测定方法可稳定测得低至<0.01的游离分数,但需综合考量各方法的适用场景与局限性。历史上,监管机构将fu的下限设定为1%,用于预测高度结合化合物的DDI。这导致了对高度结合化合物的DDI预测出现很高的假阳性。2024年5月发布的ICH M12 DDI指南允许使用实验性fu值来预测高度结合化合物的DDI。那么使用实测fu值进行DDI预测,是否会发生假阴性呢?
研究机构为了进一步增强使用实验fu值预测高度结合化合物DDI的信心[6],通过对9种高结合药物(fu < 1%)的评估发现:使用实测fu值进行预测时,采用机理模型所有临床相关DDI (效应量>20%)均被成功识别(无假阴性),采用基础模型仅阿莫伦特 (almorexan) 对CYP2D6的抑制未被预警。但即使采用1%下限,该风险仍未被识别,说明此漏报与fu测定无关,可能涉及代谢物抑制等其他机制。研究证实,实测fu的应用不仅避免了假阴性,还显著减少了传统1%下限导致的假阳性预测,这些发现不仅验证了ICH M12指南的前瞻性,更为完善高结合药物的DDI预测方式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结语
血浆蛋白结合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影响药物的分布和排泄,也关系到药物相互作用的预测。精准的血浆蛋白结合测定是优化药物相互作用预测的核心,从而有助于提高药物研发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临床试验,降低患者风险,最终实现更高效、更安全的药物疗法开发。药明康德DMPK可提供多种准确测定化合物PPB值的方法,结合ICH M12新规,为客户提供高结合药物DDI风险评估的可靠解决方案,为体内参数的预估及DDI预测提供更可靠的参考,助力降低研发风险。
作者:陆春红,王洁,王翔凌,陈根富
编辑:富罗娜·克里木,钱卉娟
设计:倪德伟,张莹莹
药明康德DMPK依托中国(上海、苏州、南京和南通)和美国(新泽西)的研发中心,提供从早期筛选、临床前开发、到临床研究阶段的综合型药代动力学服务,助力您快速推进药物研发流程。拥有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服务超1600家全球客户,具有超过十五年的新药申报经验,已成功支持超过1700个新药临床研究申请(IND)。
点击此处与我们的专家进行联系。
参考
[1] Jones RS, Leung C, Chang JH, Brown S, Liu N, Yan Z, Kenny JR, Broccatelli F. Application of empirical scalars to enable early prediction of human hepatic clearance using IVIVE in drug discovery: an evaluation of 173 drugs. Drug Metab Dispos. 2022 May 30: DMD-AR-2021-000784.
[2] Di Li. An update on the importance of plasma protein binding in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Expert Opin Drug Discov. 2021 Dec;16(12):1453-1465.
[3] Schulz JA, Stresser DM, Kalvass JC. Plasma protein-mediated uptake and contradictions to the free drug hypothesis: a critical review. Drug Metab Rev. 2023 Aug;55(3):205-238.
[4] Di, Li et al. Industry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Protein-Binding Methodologies: Considerations for Regulatory Drug-Drug Interaction and Related Guidelines on Highly Bound Drugs.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106 12 (2017): 3442-3452.
[5] Rolan PE. Plasma protein binding displacement interactions – why are they still regarded as clinically important? Br J Clin Pharmacol.1994;37(2):125–128.
[6] Tess, D., Harrison, M., Lin, J. et al. Prediction of Drug-Drug Interactions for Highly Plasma Protein Bound Compounds. AAPS J 27, 13 (2025).
[7] Fahmi OA, Hurst S, Plowchalk D, Cook J, Guo F, Youdim K, Dickins M, Phipps A, Darekar A, Hyland R, Obach RS.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for predicting clinical drug-drug interactions, based on the use of CYP3A4 in vitro data: predictions of compounds as precipitants of interaction. Drug Metab Dispos. 2009 Aug;37(8):1658-66.
加入订阅
获取药物代谢与药代动力学最新专业内容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