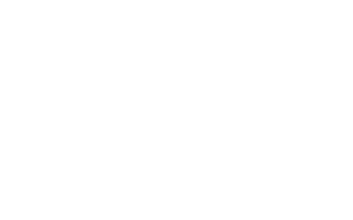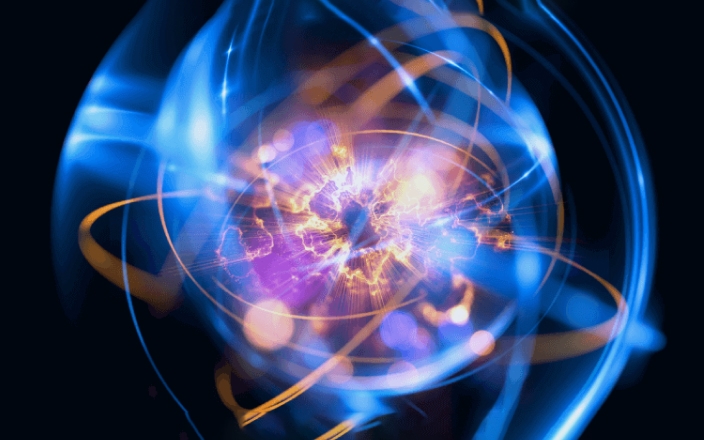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成年人的皮肤面积大约2m²,经皮肤给药后,药物会渗入皮肤各层或进入体循环产生局部或全身治疗作用。产生全身治疗作用的经皮给药称为透皮给药系统(Transdermal drug delivery systems,TDDS) [1],是仅次于口服和注射的第三大给药系统。透皮给药与临床常见口服、静脉等常规给药方式相比,具有以下优势[2-5]:
-
避免肝脏的首过效应和药物在胃肠道的降解,减少用药的个体差异;
-
维持恒定的有效血药浓度,避免了口服给药等引起的血药浓度峰谷现象,降低了毒副反应;
-
给药途径既方便又具有缓释作用(适用于生物半衰期短,需频繁口服或非肠道给药的药物),可减少给药次数,延长给药时间,灵活给药(可随时中止),特别是对于不易服药的病人,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
TDDS是采用不同给药途径的新型制剂,发展迅速,应用市场前景广阔。本文将介绍透皮制剂研究概况及相关指导原则,透皮给药的局限和药物透皮的促渗方法,以及评估透皮制剂在临床前体内PK实验中,DMPK具备的相关研发能力。
一、透皮给药制剂研究概况
1.1 透皮药物研究进展
透皮给药制剂除了发挥局部治疗作用的膏剂、喷雾剂、凝胶剂等外,还有发挥全身治疗作用的TDDS(通常指透皮贴片)。据爱尔兰市场研究机构预计,到2024年底全球透皮给药市场将达到73.58亿美元。在2018年1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在生物医学工程产业领域,透皮和黏膜给药制剂新剂型工艺技术基础研究被列入重点产品和服务[17]。
1979年东莨菪碱(Transdermscop)透皮贴经FDA获批上市,开启了现代化TDDS的篇章。目前为止,部分TDDS类产品已经获批上市,适应症主要集中在精神神经,抗炎镇静等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创新,临床用药的需求增加,透皮贴剂在帕金森、老年痴呆、抑郁病症、精神分裂症、抗炎镇痛等领域会获得更加广泛的发展。为TDDS产品申报上市提供法规支持,FDA及欧盟均有TDDS类指导原则发布[6],表2罗列了历年来FDA和EMA发布的关于TDDS的指导原则,从透皮制剂的研究生产,到制剂质量评价,安全性评价,产品包装及TDDS新药和仿制药的研发生产等方面逐步完善了监管要求。中国TDDS可参考的指导原则少,随着中国透皮制剂研发产品的递增,关于TDDS的相关指导原则也会逐渐完善。
|
NMPA |
利斯的明透皮、格拉司琼、罗替高汀、奥昔布宁、可乐定、丁丙诺菲、芬太尼、雌二醇 |
|
FDA |
利斯的明、雌二醇、丁丙诺菲、芬太尼、东莨菪碱、可乐定、硝酸甘油、尼古丁、格拉司琼、罗替高汀、哌甲酯、司来吉兰、睾酮 |
|
EMA |
丁丙诺菲、芬太尼、雌二醇、利斯的明 |
表1. 全球获批上市的TDDS产品[7]
|
FDA |
EMA |
|
2011年,《透皮和相关的药物传递系统残留药物的行业指南》 |
1999年,《缓控释类产品质量控制指导原则(A口服制剂;B透皮贴剂)》 |
|
2018年,《ANDA透皮和局部递药系统黏附力评估》和《ANDA透皮和局部递药系统刺激性和致敏性潜力的评估》 |
2010年,《关于修订释药口服剂型和透皮给药剂型质量指南的概念文件》 |
|
2019年,《透皮和局部递药系统——药品研发和质量考量》 |
2014年,《透皮给药系统质量指导原则》 |
表2. FDA及EMA的TDDS指导原则
1.2 透皮药物的促渗方法
透皮制剂是当今一大研究热点,未来市场潜力巨大,但是透皮制剂在研究中也存在诸多困难。皮肤的天然屏障,使大部分药物难以渗入到皮肤内部,导致药物起效慢,传统皮肤制剂也受到分子量,脂溶性的限制,例如亲水性药物和大分子药物等[6,8]很难渗透穿过皮肤起效。为了促进药物的皮肤渗透性,通常采用加入化学促渗剂的方法[1]和物理促渗方法[9,10](表3),且以上两种方法对于小分子及亲水性化合物的促渗效果都较为明显;对于大分子药物,分子量大,构象灵活,稳定性和递送方式是研发过程的两个难题,现在开发的剂型主要是注射剂,临床患者依从性低。大分子药物是否可以开发成透皮制剂,实现皮肤递送呢?
|
促渗剂 |
物理促渗方法 |
|
二甲基亚砜,月桂氮 |
离子导入法 |
|
乙醇、丙二醇 |
超声导入法 |
|
普朗尼克、十二烷基硫酸钠、吐温80 |
激光促透法 |
|
小檗碱、黄连碱 |
电致孔法 |
|
薄荷醇、枫香油 |
电渗法 |
|
内酯,木瓜蛋白酶、壳聚糖类 |
微针技术 |
表3. 促渗剂种类及物理促渗方法
随着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不断迭代,新的科学技术赋能物理促渗方法发展迅速,克服透皮制剂开发过程存在的障碍。例如,物理促渗方法新一代的技术:微针技术,该技术借助微针刺穿皮肤最外层,递送药物到真皮层,可以克服皮肤屏障并产生可逆的微通道以实现有效的大分子渗透,尤其是多肽,蛋白,大分子类药物的透皮传递,可以解决生物大分子药物给药难的现状。微针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寡核苷酸输送、疫苗输送、胰岛素输送、和化妆品等领域的研究[10-12]。

图1. 微针的5种分类[10]
图2是使用切除垂体的大鼠作为动物模型,使用微针贴片和SC注射给予rhGH(重组生长激素)的药代动力学结果,由图2(A)可得,大鼠血浆中rhGH浓度在微针贴片应用6小时后达到峰值浓度,随后,血浆中rhGH浓度逐渐下降,并保持高于对照组7天以上的rhGH浓度。然而,SC注射组在0.5h时达到峰值浓度,11h后rhGH浓度降至对照组水平。图2(B)是血浆中IGF-1(促生长因子)的浓度水平,IGF-1是一种主要由肝脏产生的内分泌激素,是GH(生长激素)生理作用所必需的一种活性蛋白多肽物质,可诱导IGF-1的产生,IGF-1可用作hGH活性的生物标志物,与对照组相比,SC注射组和微针贴片组的IGF-I水平均显着升高,且微针贴片可以在15天内保持高水平的IGF-1。以上结果表明微针贴片能够很好的递送rhGH,且能实现rhGH持续释放,保持rhGH的生物活性。

图2. (A)SpragueDawley大鼠给予NaHCO3/PAA-Silk微针贴片和SC注射rhGH后血浆rhGH浓度; (B)SpragueDawley大鼠给予NaHCO3/PAA-Silk微针贴片和SC注射rhGH后血浆IGF-1浓度[19]
二、透皮制剂药代动力学研究
透皮药物的体内吸收是评价透皮制剂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借用体内外模型来评估药物的皮肤渗透性和药动学参数,可为透皮制剂开发提供研究与优化的方向。
2.1 临床前体外透皮实验(In Vitro Permeation Testing,IVPT)
体外透皮实验是使用离体皮肤或人工膜模拟制剂在生理条件下的透皮过程,通过研究外用制剂中有效成分的释放、透过量和速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制剂的临床有效性[13],有益于考查药物透皮吸收的特定影响因素,体外透皮实验行业金标准是扩散池法。药明康德DMPK已经成功地搭建IVPT测试平台。
2.2 临床前体内实验(In vivo Testing)
体内实验是选用不同动物种属经皮肤用药后,在设定时间点收集某种体液(血、尿等)或组织(真皮、皮下脂肪和皮下肌肉组织等),通过测定样品中的药物含量,可直接反映某种药物剂型的有效性和生物利用度,同时也能获取药物透皮吸收后的药代参数和生理效应。IVPT与In vivo实验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16],待筛选化合物,通过IVPT快速筛选,获取化合物透皮渗透参数,以及考察不同透皮制剂对透皮吸收的特定影响因素;优选透皮制剂需要采用In vivo实验,验证候选化合物经皮给药后的剂量、药效、制剂处方以及对皮肤的刺激,来推算临床用药剂量。药明康德DMPK已开展了很多透皮制剂的体内PK评估实验,具备以下能力:动物及给药皮肤选择与评估、不同皮肤给药策略、多点微创样品采集及处理策略,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这些内容。
2.2.1 实验动物选择与评估
在透皮制剂开发的早期阶段,模拟人体皮肤组织,最普遍被采用的是猪皮。有文献报道,猪皮在组织学和生物学的构造与人的皮肤相近,表4为不同种属动物皮肤结构比较,主要评估参数:结构、厚度,毛发稀疏性等,实验猪是最佳的实验动物透皮评估模型[14,15]。
我们多维度评估巴拿马香猪的皮肤组织,评估方向包括:皮肤外观评估、光镜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图3为所使用巴马香猪HE染色结果和各层皮肤厚度,表5为文献提供巴马香猪与人体皮肤各层厚度,获取的数据表明巴马香猪的皮肤结构与文献一致,进一步佐证巴马香猪是透皮制剂评估的最佳动物模型。
|
Criteria |
Guineapig |
Human |
Mouse |
BamaMinipig |
Rat |
|
Skinattachment |
Loose-attached |
Firmlyattached |
Loose |
Firmlyattached |
Loose |
|
Haircoat |
Sparseordense |
Sparse |
Dense(exceptsomebreed) |
Sparse |
Dense(exceptsomebreed) |
|
Epidermis |
Thick |
Thick |
Thin |
Thick |
Thin |
|
Dermis |
Thick |
Thick |
Thin |
Thick |
Thin |
|
Panniculuscarnosus |
Present |
Absent |
Present |
Absent |
Present |
|
Healingmechanism |
Contraction |
Re-epithelialization |
Contraction |
Re-epithelialization |
Contraction |
表4. 不同动物皮肤比较[15]

图3. 巴马香猪皮肤HE染色图
|
皮肤分类 |
角质层(μm) |
表皮层(μm) |
真皮层(mm) |
|
4月龄巴马香猪 |
14.900±1.370 |
84.800±3.360 |
1.271±0.068 |
|
6月龄巴马香猪 |
15.600±1.506 |
97.100±4.532 |
1.933±0.066 |
|
成人皮肤 |
15.100±1.663 |
86.200±6.579 |
1.315±0.069 |
表5. 巴马香猪皮肤与人体皮肤各层厚度比较[17]
2.2.2 实验给药策略
实验动物巴马香猪的生活习性喜欢拱、蹭,给实验保定和给药带来多项挑战。经多年技术测试和不断优化,我们自制了多种实验工具,制定了完善的操作流程和评估指标,满足不同实验的给药设计,从而保证给药操作的一致性,以及实验数据的可靠性。
根据实验设计需求,进行皮肤状态的评估。正常完整皮肤模型的实验,我们依据制定的评估标准,进行动物皮肤的评估;损伤皮肤模型的实验,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基础上,用专业的、验证过的工具造模;并根据我们已有的评估标准和依据评估皮肤损伤的程度,保证实验的可靠性。
针对损伤皮肤模型建立,药明康德DMPK也通过实验验证造模方法的可靠性,图4为巴拿马香猪皮肤HE染色图片,对比发现损伤后的皮肤确实完全去除了角质层和表皮层,图5的结果也表明,去除表皮,皮肤的屏障作用减弱,药物的皮肤渗透性会增加,对比各组药物浓度均值,发现损伤皮肤真皮层及血浆中的药物a的浓度是明显高于正常皮肤的。

图4. 巴马香猪皮肤HE染色结果(左侧为正常皮肤HE染色结果,右侧为损伤皮肤HE染色结果)

图5.不同皮肤模型真皮层及血浆中药物a的时间-浓度曲线图
A正常皮肤真皮层药物a浓度;B损伤皮肤真皮层药物a浓度;C正常皮肤血浆药物a浓度;D损伤皮肤血浆药物a浓度
2.2.3 实验样本的采集及处理
实验样本的采集及处理主要依据实验设计进行,如血样采集,针对发挥局部作用的制剂,较为关键的是皮肤样品的采集及分层操作,比如同一只动物在不同时间点连续采集系列皮肤,我们采用专业的皮肤采集器保持样本采集均一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小对动物的损伤。皮肤分层处理,我们采用冷冻切片机固定厚度皮肤分层切片。根据实际需要可分离角质层、表皮层、真皮层和皮下组织。在样品匀浆处理过程中,我们通过摸索与测试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低温珠磨法,可以获得颗粒度小,粒径相对均一的匀浆液。与传统匀浆法优劣势比较见表6和图6。
|
匀浆方法 |
优势 |
劣势 |
|
传统匀浆法 |
1. 均质效果好 2. 适用范围广,可以处理大体积 3. 处理单个样品速度快 |
1. 不好处理微量体积 2. 容易造成交叉污染 3. 容易造成小体积样本损失 |
|
珠磨法 |
1. 通量高,不会造成交叉污染 2. 可以处理微量体积 3. 具备低温操作环境 4. 样品出料粒度小 |
1. 仪器设备投入高 2. 组织样品需要前处理 |
表6. 不同匀浆方式比较

图6. 匀浆后的组织显微镜观察结果(左侧为传统匀浆法处理后得到的组织;右侧为珠磨法处理后的组织)
结语
透皮给药对比经口或注射等给药途径,应用更便利和灵活,提高了受试人群的依从性和安全性。因此,TDDS成为药物研发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伴随着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迭代,TDDS应用场景,从单一的小分子药物递送,延伸到生物类药物的递送,尤其像胰岛素、疫苗、DNA这样典型的大分子药物将有望通过透皮给药系统在各类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中发挥重要作用。药明康德DMPK在过去4年已经完成超过30个透皮制剂,200多只动物的体内PK实验,具备丰富的透皮制剂体内PK实验经验,能够助力透皮制剂研发,推进透皮制剂研发进程。
药明康德DMPK依托在中国(上海、苏州、南京和南通)和美国(新泽西)的研发中心,提供从早期筛选、临床前开发、到临床研究阶段的综合型药代动力学服务,助力您快速推进药物研发流程。拥有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服务超1500家全球客户,具有超过十五年的新药申报经验,已成功支持超过1200个新药临床研究申请(IND)。
点击此处可与我们的专家进行联系。
作者:裴琳琳,何欢,张超,李志海,刘守桃
编辑:方健,钱卉娟
设计:倪德伟
参考
[1]包玉胜. 透皮给药系统的研究进展[J].山东化工,2014,43(06):58-61.
[2]崔福德. 药剂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3] Y. T. Zhang, M. Q. Han, L. N. Shen, et al.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formulated for transdermal aconitine administration and evaluated in vitro and in vivo[J]. Biomed Nanotechnol. 2015. 11, 351.
[4] T. A. Ahmed, K. M. El-Say, B. M. Aljaeid,e tal. Transdermal glimepiride delivery system based on optimized ethosomal nano-vesicles: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in vitro, ex vivo and clinical evaluation. Int [J]. Pharm. 2016. 500, 245.
[5] S. Meng, C. Zhang, W. Shi, X. et al. Preparation of osthole-loaded nano-vesicles for skin delivery: Characterization, in vitro skin permeation and preliminary in vivo pharmacokinetic studies. Eur [J]. Pharm. Sci. 2016. 92, 49.
[6]王秀杰. 透皮给药(TDDS)产品及法规概述[J].海峡药学,2021,33(06):210-212
[7]刘孟斯, 姜典卓, 岳志华, 周誉. 国内外透皮贴剂申报上市进展及药学研究探讨[J].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2021,38(08):866-869.
[8]万展, 周剑, 韩美娜等. 微针透皮给药系统应用研究进展[J].药学实践杂志,2012,30(02):86-88,142.
[9] Donnelly R F, Singh T R R, Woolfson A D. Microneedle-based drug delivery systems: microfabrication, drug delivery, and safety.[J]. Drug Delivery, 2010, 17(4):187-207.
[10] Liu T, Chen M, Fu J, 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microneedles-mediated transdermal delivery of protein and peptide drugs[J]. 药学学报:英文版, 2021, 11(8):18.
[11] Ding Z, Riet E V, Romeijn S, et al. Immune Modulation by Adjuvants Combined with Diphtheria Toxoid Administered Topically in BALB/c Mice After Microneedle Array Pretreatment[J].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2009, 26(7):1635-1643.
[12] Sullivan S P, Koutsonanos D G, Martin M, et al. Dissolving polymer microneedle patches for influenza vaccination[J]. Nature Medicine, 2010, 16(8):915-920.
[13]李郭帅. 复方南星止痛膏体外透皮吸收及质量标准提升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2019. [14]Jacobi U, Kaiser M, Toll R, etal. Porcineear skin: an in vitro model for human skin. [J]. Ski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2010, 13(1):19-24.
[15] Summerfield A, Meurens F, Ricklin ME. The immunology of the porcine skin and its value as a model for human skin. Mol. Immunol 66, 14–21 (2015).
[16]杜建平, 陈济民. 药物透皮吸收研究的实验方法[J]. 中国药学杂志, 1988, 23(6):323-327.
[17]陈俊颖, 胡俊西, 魏泓. 人与巴马香猪皮肤的比较生物学研究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05, 16(5): 288-289.
[18]王君平. 透皮给药 产品未来市场空间大[N]. 人民日报. 2020-05-03(6).
[19] Li Y A, Ql A, Xw A, et al. Actively separated microneedle patch for sustained-release of growth hormone to treat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J].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2022.
加入订阅
获取药物代谢与药代动力学最新专业内容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