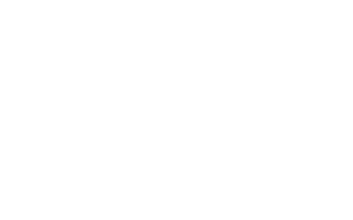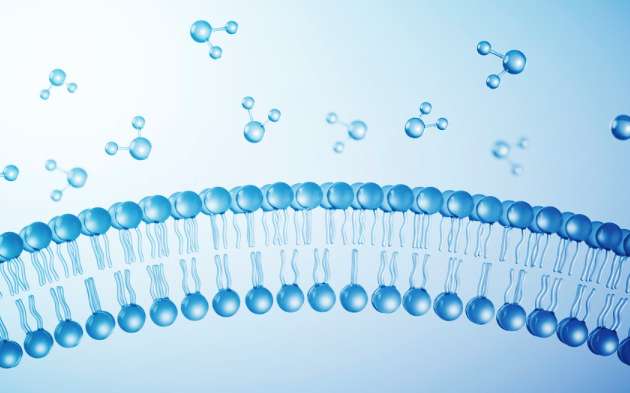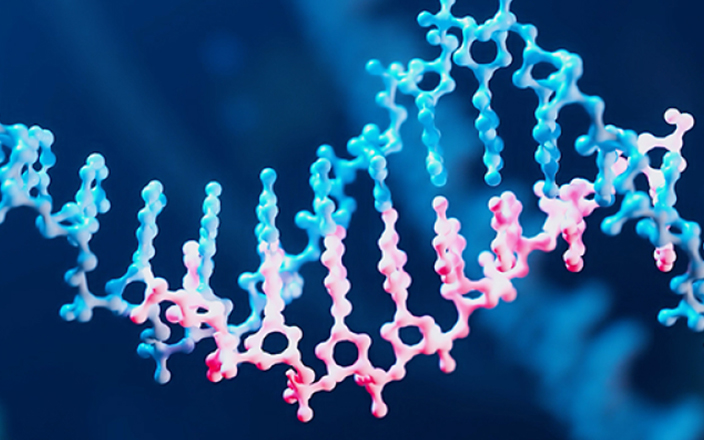随着近几年指导原则的相继出台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研究的普及,CYP酶诱导能力评估在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尤为凸显。但是随着大家对最新的指导原则的解读,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现了,特别是如下的观点——既然2020年终稿的FDA指导原则以及2021年试行的NMPA指导原则中仅有mRNA的测定标准,即“体外系统,在研药物孵育后,测定CYP酶的mRNA表达水平倍数变化,以评估在研药物是否为酶的诱导剂。”那么还需要进一步监测酶活性水平的变化吗?
针对此观点,我们的回答如下:
根据指导原则的变化历程来看,酶活性自始至终都是备受关注且广泛使用的指标。
从中心法则的角度来说,mRNA的水平变化会早于酶活性的变化,因而早期的筛选实验可以仅采用mRNA水平评估。
单一的指标容易受不同的影响因素干扰,酶活性指标容易受化合物本身是抑制剂干扰,而mRNA指标容易受化合物存在基因下调可能性的影响,因而申报阶段需要同时考察两个指标。
CYP酶(细胞色素P450酶)是一类存在于人体内参与许多重要的生物化学过程(尤其是药物代谢)的酶系。研究CYP酶诱导作用的意义包括:影响自身药物代谢的速度,从而影响药物的药效和潜在毒性;影响其他合用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同时更好地理解CYP酶差异引起的个体代谢差异。
体外研究(例如使用人肝细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哪些药物可能诱导CYP酶,以及其可能产生诱导的程度。这些体外数据可以用来预测在人体内可能发生的药物相互作用,为临床药物使用提供指导。那么具体应该如何从体外的数据评估对应的CYP酶诱导程度呢?
根据FDA指导原则的发展历程看,CYP酶活性一直是重要的指标。
药物相互作用的指导原则从初版至今已经历了数次的更新改版。在初版(1997)的药物指导原则中,只简略的概述了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方向,并未具体地说明研究方案及实验设计等,而在后续的指导原则中,则不断地丰富了这些具体的内容。下文将阐述受试药物由CYP450酶介导的诱导作用判定标准在FDA 指导原则中的变化历程。
2004版的FDA 指导原则初次提出研究药物诱导潜能最可靠的方法是量化原代肝细胞培养后的酶活性变化,并且给出判断指标是受试化合物相对于基质对照的诱导倍数,或是相对于阳性对照的活率百分比。当药物产生2倍以上的酶活性增加或超过阳性对照的40%的百分比变化时,可以认为该药物是酶的诱导剂[1]。
在2006版的指导原则中,对体外酶诱导实验的设计有了更详细的描述。对于酶活性变化的判断,删去了相对于基质对照诱导倍数增加大于2倍的说法,只留下了相对于阳性对照的变化大于或等于40%即被认为是酶诱导剂的说法。至此,关于酶活性的诱导判定标准则不再出现修订[2]。
在2012版中,首次新增用待测药物测定不少于三个供体的人肝细胞的mRNA的变化作为CYP酶诱导的评估判断的重要指标。这是由于当酶诱导和酶抑制作用同时存在时,酶诱导效果很可能被掩盖,而mRNA的测定则可以对此掩盖现象的解读有所帮助。只是,此版本中并未对mRNA变化的判定标准作出明确说明[3]。
到了2017版本,在mRNA水平判定标准上,该版较前一版有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当mRNA相对于基质对照增加≥2倍且≥20%阳性对照倍数时被判定为CYP酶的诱导剂。当诱导作用在其中一个供体中存在时,都应当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实验[4]。
最后,终版2020年指导原则中,mRNA水平的倍数变化成为首要判定诱导的标准,同时酶活性水平的检测也作为可接受的判定指标。对于诱导的判断,则主要以下述标准执行“当CYP酶的mRNA水平在经受试药物处理后呈浓度依赖性增加,且大于等于2倍基质对照时,判断为该CYP酶的诱导剂,而当mRNA的水平增长小于2倍,但相对于阳性对照的百分比大于20%时,也不应该排除其诱导潜能,应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5]。

图1. FDA 2020指导原则《体外药物相互作用研究——细胞色素 P450 酶和转运体介导的药物相互作用指导原则》
从整个指导原则的变化历程中可以看出,目前评价CYP酶诱导的两大标准依旧是酶活性的测定以及目的基因的mRNA水平的改变。近几版的指导原则的判定标准,重心逐渐倾向于mRNA水平的改变(表1),但酶活性变化一直作为一种最广泛的方法被使用。
表1. 从2006年至2020年FDA指导原则中关于CYP酶诱导的指标和判断标准的变化
指导原则版本 | 指标 | 判断标准 |
2006 | 酶活性 | A drug that produces a change that 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40% of the positive control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enzyme inducer in vitro and in vivo evaluation is warranted. |
2012 | mRNA | If the in vitro induction results are positive according to predefined thresholds using basic models, the investigational drug is considered an enzyme inducer and therefore further in vivo evaluation may be warranted. |
2017 | mRNA | A ≥ 2-fold increase in mRNA and a response ≥ 20% of the response of the positive control in the presence of an investigational drug are interpreted as a positive finding. |
2020 | mRNA | A drug is interpreted as an inducer if: (1) it increased mRNA expression of a CYP enzyme in a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manner; and (2) the fold change of CYP mRNA expression relative to the vehicle control is ≥ 2-fold at the expected hepatic concentrations of the drug. |
从CYP酶诱导的机理来说,通常mRNA的水平变化会早于酶活性的变化,因而早期筛选可以仅选用mRNA水平作为研究对象。
CYP的诱导通过核受体或类固醇受体超家族的3个“孤儿受体” (orphan receptors)进行。芳烃受体、孕激素核受体和雄激素是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可调节CYP的表达。
具体过程如下:一旦核受体被激活,DNA 中的基因被转录为前体 RNA (pre-mRNA)的能力变强,前体 RNA 通过剪接、加帽和尾巴化等步骤,成为成熟的 messenger RNA (mRNA)。mRNA 离开细胞核,进入细胞质,被肽链延伸因子 (polymerase) 翻译为多肽链,即蛋白质。多肽链折叠为三维结构,成为功能性的蛋白质,其中包括酶。以CYP1A2的调节为例,见图2。

图2. AhR核受体调节CYP酶表达示意图[6]
这个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mRNA的稳定性、翻译效率、蛋白质的后修饰等。因而在早期筛选阶段,建议采用较早受到上调的mRNA水平作为评价CYP酶诱导能力的指标,可以对前期化合物的筛选有较为灵敏地评估。
当然,单一的指标总有其局限的地方,因而即使是早期筛选阶段也是建议多个浓度开展,可以有效避免mRNA检测中的局限性。
单一的诱导指标容易受不同的影响因素干扰,比如酶活性指标容易受化合物本身是抑制剂等干扰,而mRNA指标容易受化合物存在基因下调可能性的影响,申报阶段需要同时考察两个指标。
从指导原则的迭代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因为考虑到酶活性会受到受试化合物本身是CYP酶的抑制剂,特别是TDI抑制剂的影响,所以增加了mRNA水平的指标,并且逐渐以mRNA水平变化判断为主。但是在mRNA水平研究时,也发现了非细胞毒性引起的基因下调的现象,因而仅采用一个浓度,特别是较高浓度进行CYP酶诱导水平评估时,依旧会有假阴性的结果,如图3所示[7]。

图3. 受试化合物在不同浓度下对CYP酶mRNA水平和酶活性水平的诱导作用
当然两个指标同时采用时,会出现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一旦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建议结合化合物的其他数据进行解读。总体来说,主要分为以下六种情况[7]:
Example 1:典型的阳性诱导剂的表现
Example 2:在酶活性和mRNA水平均没有诱导作用
Example 3: 在酶活性和mRNA水平均有诱导作用
Example 4: 在mRNA水平有诱导,而酶活性水平无诱导,考虑化合物可能同时是该酶的抑制剂
Example 5: 在mRNA水平无诱导,而酶活性水平有诱导,考虑化合物可能使得mRNA不稳定
Example 6: 在mRNA和酶活性水平均下调,考虑化合物抑制CYP酶的基因表达。

图4. 6种情况详细解读
药明康德DMPK依托在中国(上海、苏州、南京和南通)和美国(新泽西)的研发中心,提供从早期筛选、临床前开发、到临床研究阶段的综合型药代动力学服务,助力您快速推进药物研发流程。拥有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服务超1500家全球客户,具有超过十五年的新药申报经验,已成功支持超过1200个新药临床研究申请(IND)。
点击此处可与我们的专家进行联系。
作者:孙颖,姜利芳,陈根富
编辑:钱卉娟
设计:倪德伟,张莹莹
参考
[1]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ug Interaction Studies —Study Design, Data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for Dosing and Labeling. October 2004.
[2]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ug Interaction Studies —Study Design, Data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for Dosing and Labeling. September 2006.
[3]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ug Interaction Studies —Study Design, Data Analysis, Implications for Dosing, and Labeling Recommendations. February 2012.
[4]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In Vitro Metabolism- and Transporter- Mediated Drug-Drug Interaction Studies. October 2017.
[5]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In Vitro Drug Interaction Studies-Cytochrome P450 Enzyme- and Transporter-Mediated Drug Interactions. January 2020.
[6] Bach L.TOLERANCE DIFFERENCES BETWEEN SIBLINGS OF THE POLYCHAETE SPECIES COMPLEX CAPITELLA CAPITATA TO THE PAH, FLUORANTHENE[J]. 2005.DOI:10.13140/RG.2.1.4538.8964.
[7] Wong, S. (2021). Determination of In Vitro Cytochrome P450 Induction Potential Using Cryopreserved Human Hepatocytes. In: Yan, Z., Caldwell, G.W. (eds) Cytochrome P450. Methods in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Humana, New York, NY. https://doi.org/10.1007/978-1-0716-1542-3_12
加入订阅
获取药物代谢与药代动力学最新专业内容和信息